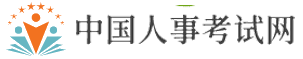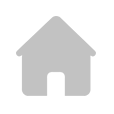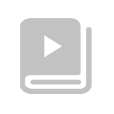自从物权行为理论诞生,理论界便一直对其褒贬不一,主如果一定物权行为与否定物权行为之争占主流。一定者觉得,在一个买卖过程中,第一设立债权行为,产生债权债务关系,而欲使其物权变动,还需有一个独立的物权行为,即移转物权意思的出货行为。物权行为使法律行为规范得已健全,使不当得利请求权有了法理基础,更为要紧的是,物权行为独立性理论为买卖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而否定物权行为者则觉得,物权行为中的意思表示并不具备独立的意义,债权行为中的意思才具备独立意义。而且出货行为只是事实行为(realakte),并不可以说明物权行为具备独立性,因出货行为而引起的物权变动是债权行为的当然成效。再者,物权行为理论过于复杂玄妙,很难为公众学会理解,其把日常简单的财产出售分解为数个独立的法律行为,使现实法律生活复杂化,对法律适用不利,且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使出卖人的所有权返还请求权转化为不当得利请求权,对出卖人来讲极为不利,有失公平。[1](123-124)一定物权行为与否定物权行为两种看法的争论,直接涉及到对民法出货行为法律性质的确定:若一定物权行为,则出货行为能产生物权变动之法律成效;若否定物权行为,则出货仅为履行行为或事实行为,并不影响物权变动。因此,笔者觉得,对出货行为的性质界定,需要从对两种看法的考察上予以剖析,不然,便没办法得出一个让人信服的结论。
1、物权行为意义上的出货行为
需要声明的是,这里是以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为首要条件条件的。根据一定说的看法,债权契约的效力在于设定当事人的负担行为,并不产生物权变动成效。要发生物权变动,就需要依靠于债权契约以外的一个可以达成物权变动的行为,这一行为即为物权行为。债权契约行为与物权变动行为彼此离别,各自独立,使得物权行为具备其独立性。
罗马法时期,刚开始移转物的所有权的出货需要需要有让与人与受叫人之合意。“由于一物的授受,在法律昌明时期,可为各种推定,或为出租,或为寄存,或为出质,或为出卖,或为增与等。其所产生的成效,或仅给予持有,或为占有些让与,或为所有权的转移,所以出货要有合法是什么原因,以证明所有权因出货而转移,不然,当事人没转移所有权的意思,则只能发生占有或持有些成效。”[2](337)到帝政时期,因为法律进步,其合法缘由发生了变化,“只须当事人有转移所有权的意思,出货即可生效。即便借以出货的法律行为因违法、错误等而无效或有缺陷时,也不影响所有权移转的效力。”[2](337)这充分说明了,早在罗马法时期,法学家们已经注意到了物权移转的合意与出货的离别状况,不只讲究缘由是不是合法,更强调出货的法律效力,甚至在缘由的违法情形之下也不影响出货之移转物权成效。其实,这种规范所不可以克服的弊病在于,物权是不是转移仅在于物之是不是出货,对在出货之前的契约的保护便看上去薄弱。伴随经济的进步和商业的兴盛,这种契约保护薄弱的现象直接妨碍着社会的进步。买卖的进行,并不是皆为即时出货,还需要有对尚未履行的契约给以保障的法律。于是尊重私法上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以保护契约便成为一项常见的民法原则。至此,契约变成了受法律保护的债权行为,可拘束缔约的双方当事人。而出货则形成移转物权的法律行为,可产生物权变动成效。
事实上,从某个买卖过程来看,要达成物权之变动,确实要历程这两个被抽象的阶段。因此,与其说这是立法上确认物权行为之独立存在,不如说是买卖经验的自然现象更为适合,只不过这种买卖上的自然现象让人为分割并被法律所固定。如《德国民法典》第929条第1款规定:“为让与一项动产的所有权,需要由物的所有人将物出货于受叫人,并就所有权移转由双方成立合意。”该条规定说明,一个以移转物权为目的的买卖让人为分割为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并以出货为物权行为表征分别给予了法律上的规范。①将物出货于受叫人,其中当然包含移转物权之合意,若无合意,其出货便不可以完成,其买卖目的便不会达成。其实在债权契约中就已包括移转物权之意思,而在出货行为中亦包括有移转物权的意思。这两个阶段的移转物权意思本没有明显的界限或性质的不同,将它分隔,只不过人为的抽象的定义,目的是为了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分别予以法律保护。现实日常,若当事人之间无物权移转之争议,则这种抽象的划分并无实质意义。“由于假如把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从公示行为中独立出来,出货就是一个无具体意义的动作。”“同样假如把它从债权行为中独立出来,债权契约所内含的就只不过当事人欲请求他们出货的意思表示,对物权是不是移转的企图并不可以被包括。这就把本来具备内在联系的物权变动过程,人为地分割成三个独立阶段,实在有违大家生活之常情。”[3]因此,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在法律保护上就具备了明确的法理基础。同时,也就确立了出货行为可在法律上作为移转物权的效力意义。
以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为基础,无疑使得物权行为成为法律意义上的行为,而出货不只有移转物权的意思,同时也是物权变动的表象,其当然也符合法律行为的特点。在法律保护方面,可就出货行为作出专门性的规定,明确只有出货行为才具备移转动产物权之法律效力。只是在动产出货过程中,移转物权的意思可通过出货行为推定,其并没有明显的意思形式和物权形式之分,甚至只是定义上的意义。出货本身就是表意和出货行为的结合。一个真实的物权变动如依靠于一个有效的债权契约,只不过有了移转物权的可能性,即债权契约中的债务人获得了对物的占有些请求权,到底达成与否势必依靠于物权行为即出货。也就是说“物权移转的成效一定系于出货行为,在不动产则为登记行为。”[4](39)而且,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意味着出货行为不止是物权行为的移转方法,而且还兼具物权变动公示之效力。出货为物权变动过程,其结果是移转占有和受让占有,使物权移转具备叫人知道的外在表象。“占有之所在即为动产物权之所在”[5](58)故出货显然可以作为物权变动之分界线,具备公示物权变动状况之成效。总之,出货作为物权的移转形式存在于物权行为理论中,尽管其具备肯定的缺点,但这只是法律规范进一步健全的问题,明确出货行为可作为物权变动之法律行为,从法律意义上来讲人,仍具备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2、债权行为意义上的出货行为
以移转物权为目的而设立的契约有效成立后,其物之所有权即行转移,而为达成占有而出货标的物的行为乃债权行为意义上的出货行为。不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之立法模式的代表当属法国民法体例。《法国民法典》第71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因继承、生前赠与、遗赠与债的成效而获得或移转。”第938条规定:“经正式承诺的赠与依当事人间的合意而即完成;赠与物的所有权因此即移转于受赠人,无须再经现实出货之手续。”第1583条规定:“当事人双方就标的物及其价金相互赞同时,交易合同即告成立,而标的物的所有权依法由出卖人转移于买受人。”这里对物之是不是出货,并不影响买卖契约的有效成立,且对物权之移转也不依出货行为为必要。此种立法例表目前私法上就是保护意思自治及买卖自由。在物权法上,契约中之物权移转意思直接延续至物权变动,即债权行为直接产生物权移转效力。法国法上的物权移转成效并不是单纯地来自债权行为即债权契约,只不过立法上将物权移转之意思统一于债权行为之中。实质上,其物权移转成效仍然源自双方关于移转物权之合意即契约,在此情形下,便无承认物权行为独立存在之必要。由此推论,“在法国法上,合同履行中的出货的意义远没离别主义立法上合同的履行意义重大:它不光是法律认同完成物权变动的必要形式(由于物权公示的法定化是物权法定的要紧内容),而且还是物权对世性的合理依据。”[6](43)出货行为并不是是具备独立意义的法律行为,而只是履行契约的纯粹的事实行为。
认可法国立法模式者,还有《日本民法典》,该法典第176条规定:“物权的设定与移[tsy1]转,只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效力。”第178条规定:“关于动产物权的出售,非有其动产的出货,不能以之对抗第三人。”虽然与《法国民法典》相比稍有不同,但其本质上是一致的,即物权变动依契约合意而成立,出货不再具备移转物权的外化特点,只不过一个移转物权的占有些事实行为。由于“占有是一种事实,所以,占有些移转就需要以出货这一物质的形式,至于所有权就无须这样,只须有单纯的观念形态的合意就能发生移转……观念所有权的强化,使得出货要件遭到了抑制,从而使得所有权的移转行为被观念的债权契约所吸收,使之成为债权行为的成效构成。”[7](35-36)债权契约本身便包括着观念性的物权移转,若将本为一体的物权移转抽象成不同阶段,只不过复杂了物权移转的内在原因,对现实生活却无多大帮助。董安生先生曾对此有较为精辟的论述:“尽管在民法理论上可以将物权行为的内在原因抽象为意思表示和事实行为‘两项要件’,但在现实形态上却需要将它理解为一项行为。试图将物权行为中所的含义表示和出货登记行为割裂为两项行为,或者试图单纯以合意来讲解物权行为都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出货也好,登记也好,其中势必包括有意思表示原因,此种意思表示在未遭到法律调整时势必采取默示或践行的形式,这正是物权行为定义据以打造的理论依据。”“物权行为中所的含义表示在法律意义上是对债权行为意思表示的重复或履行,它不可能具有悖于债权行为的独立内容。”[8]
[1][2]下一页